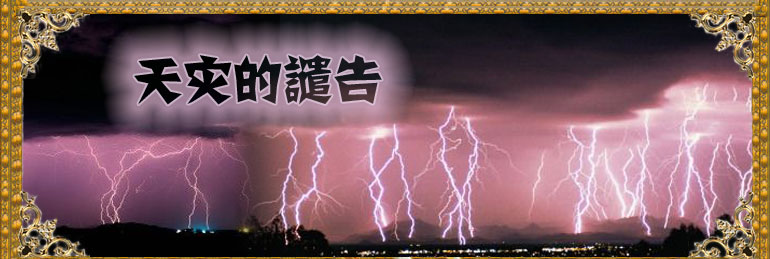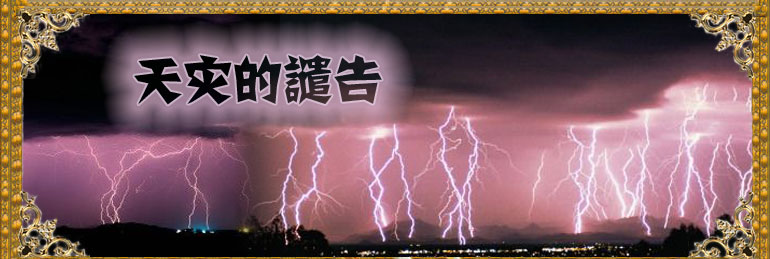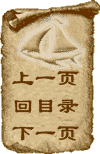|
《竹书纪年》记载了周厉王二十二到二十六年间西周发生的连续五年大旱,描述这场大旱“大旱既久,庐舍俱焚”。《诗经》也描述这场大旱灾“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民之无良,相怨一方。”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是周朝残暴的君王,以专利塞言遗臭历史。厉王贪财好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厉王:“周王室要衰微了啊。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知道大祸临头。财利,万物所生,天地所载,人要独占,必然祸患降临。天地间生成的万物,人人都应有所享有,怎么可以独占呢?招致了很多人的怨,却又不知防备大难。荣公这么做,君王能安宁长久吗?作为君王,应该开发财利,普施天之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即使如此,也还要日日小心惶恐,以防天怒人怨。所以《颂》诗说:‘后稷盛大文德,行合天地之意,利施天下万民,无不遵循正道。’《大雅》说:‘周朝基业立于广施万民而还要惶恐。’这不正是说让万民各得其所而还要谨慎防备大难,因此有今日的周朝基业。而如今君王去独占财利,这怎么能做呢?普通人独占财利,被称之为强盗;君王如此做,就没有人会归顺。荣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要败亡。”厉王不听劝谏,终以荣公为卿士助厉王独占财利。
历王如此行为暴虐,奢侈专横。就有百姓公开议论他的恶行。召公劝谏说:“百姓已难以忍受了。 ”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命令他监视那些议论他的人,发现了后就报告,立即处死。这样议论的人少了,可是四方诸侯也不来朝见了。后来,厉王变得更加严苛,百姓没有谁再敢开口议论,在路上相见也只相交换眼色示意而已,以免被报告议论厉王而招致死罪。厉王见此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平息所有百姓对我的议论,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召公说:“这只是强行堵塞。堵塞百姓言论,比堵塞水流更危险。水流堵塞后一旦决口,会伤害更多人;堵塞百姓的言论,道理是一样的。因此治水的人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百姓的人,也应该放开言路,让他们敢于说话。所以天子治理国政,使公卿直到列士都能献出讽喻的诗篇,盲人乐师献出反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要献可资借鉴的史书,太师要献箴戒之言,由盲人朗诵这些所献的诗书和箴戒之言,让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百姓可以把意见上传,天子近臣能尽行规谏职责,内亲外戚也能监察过失,乐师、太史能以乐曲和历史告诫劝导,大臣中的长者帮助整理所有的意见,然后由天子权衡斟酌而行,这样所有政事都能顺利施行而不出错。百姓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一切财用都源于这里;百姓有口,又好像大地有丰田沃野,衣服粮食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把话从口说出来了,政事是错是对也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从而督促施行善政而防备恶政,就像大地出财用,出衣服粮食一样。百姓心里有思虑,由口吐露出来,可以去采纳利用。可如果非要去堵塞百姓的口,那怎么能行。 ”厉王不听。从此百姓都不开口了,不出三年,百姓纷纷起来反抗,袭击厉王。厉王不得不出逃到彘。
《竹书纪年》有“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后来厉王就死在彘。这场大旱是周厉王这个暴君不得不放弃王位而狼狈出逃的一个直接起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