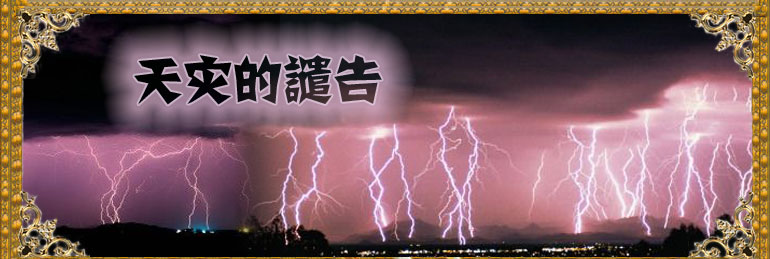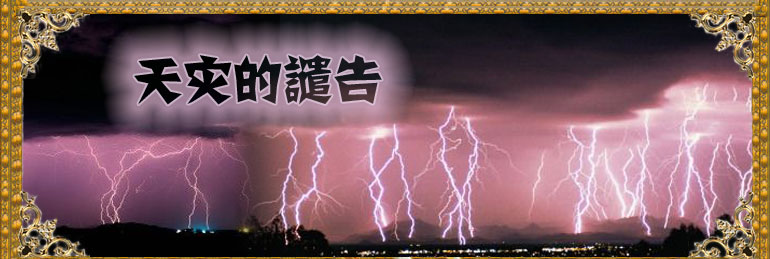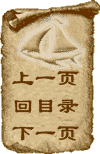|
明朝的兴亡似乎同瘟疫连接在一起。朱元璋十七岁时父母兄长死于瘟疫, 于是被迫出家加入明教,冥冥中完成了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一步。瘟疫则把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推向灭亡。
崇祯皇帝十八岁登位,面对朝廷内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权,朝廷内外社会动荡,北方清朝的紧逼,寻求治国方略,躬亲政务,努力挽救频临灭亡的明王朝。天启七年(1628年) 十一月,崇祯皇帝铲除魏忠贤党羽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中魏忠贤自缢而亡。此后宦官党羽被清除,天启年间被贬黜官员获重新起用,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赋以收复全辽重任。可是,崇祯皇帝的开明很快为残暴和刚愎自用取代。他不断加税,以至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其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有七人,巡抚有十一人。内阁重臣频繁替换,先后起用更换近五十人之多,尤其于1630年凌迟处死抗清名将袁崇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明朝末代崇祯年间的大旱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探讨过了。与全国性的大旱灾相随,瘟疫频繁暴发。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鼠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十年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范围鼠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范围鼠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范围鼠疫,同时这次鼠疫大范围传入北京,据明史记载“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于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达到高峰。
对这次北京大疫,今人有不少专门分析和历史纪录的整理,给出了一幅幅使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描述了鼠疫感染者的景象:“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被认为就是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据估计认为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州区疫情同样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京城实际上成了一座恐怖的疫城。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崇祯实录》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六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城中鬼影幢幢。
这次大疫使明朝集结在京畿的几十万重兵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据认为京营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兵员锐减,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士兵守卫。而且士兵的羸弱与人心涣散到了“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的程度。
就在这一年,即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 三月,李自成农民军轻易攻陷北京城。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陷的。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其攻陷的是一座已经被鼠疫夷平了的空城。
李自成攻取北京城后,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三十五岁。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自缢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崇祯帝把明朝的灭亡归为臣下,似乎没有意识到天意不可违。
就整个华北而言,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加上由于旱灾与蝗灾相伴随,据估计人口死亡象京城一样,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造成国力匾乏,人口稀少。面对日益强大的清军,整个中原失去了作有力抵抗的能力,清军应天时地利,顺利入主中原。
就这样在1644年这短短的一年间,朝代在瘟疫中完成了交替,历史进入了大清皇朝的顺治元年。同时,大范围的鼠疫流行很快趋于消失,华北日趋风调雨顺,社会开始复苏,为即将到来的“康乾盛世”作好准备。明亡清起,天意如是。
|